什么是炒股杠杆 生活对他开的每一个荒诞玩笑,他都给出了更荒诞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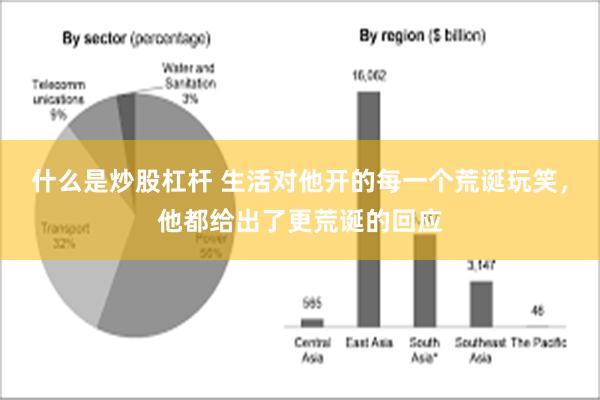
雷军称这是小米史上最强的业绩什么是炒股杠杆,不得不说在手机、家电、汽车等领域齐发力的小米真可谓是赢麻了。
其实现在国内各大手机厂商在长焦上的拍照都做得很不错,加上这几年算法的进步,基本上在超长焦拍照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一家饭店,一个舞池,一群人正双双对对地跳着波尔卡舞,人群中,一位美貌的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她梳着长长的发辫,发辫上的缎带飞扬,当她飞身旋转的时候,那缎带画出了圆圈,世界如同音乐木马一样,在她和舞伴的周围转动。他们二人正在骄傲的巅峰,感觉到其他跳舞者的动作都越来越慢,都看着他们,渐渐收住了脚步,退到一边,最后,只剩下他们俩还在继续跳。
他们脚下没停,心里的骄傲却渗入了疑心:气氛不对呀,怎么其他人看他们的神态,都不是羡慕、嫉妒,而是一脸嫌弃呢?
酒店的门砰地一开,姑娘的妈妈大踏步闯进来,一把把女儿拽走了。剩下了小伙子待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咦,空气中有一股臭味,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污水。旁观的人,有的正在费力地擦着自己被溅湿的衣服。污水哪来的?是女孩带进来的——她在跳舞中途上了趟厕所,心里激动着,不觉自己的发带、裙子垂落到粪坑里,浸淫了一遍。浑然不知的她,一回到舞厅就又纵情旋转,于是……
乡村酒店的厕所大概都无法期待。但这位名叫曼倩卡的姑娘,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酒店里。她甚至全家都搬走了,因为她在那一带已成了一个笑柄,人们都叫她“甩大粪的曼倩卡”。
只有一个人仍然在找她——是她的那位舞伴,他想请求曼倩卡的原谅,他想说声“对不起”:我把你带来这家酒店,结果却让你丢丑;我不但要娶你,我还要把你写进我日后的小说里,让我的读者都知道,你有多么美。
这本小说,他写成了,名字就叫《过于喧嚣的孤独》。
恶作剧式的转化
我喜欢把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本人,看作他最著名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的主人公,这个人,一大把年纪了,一直在絮絮叨叨说他自己的事,说他事事倒霉、处处碰壁的生活。他说:我是个法学博士,还懂拉丁语,可是我一直干一些用不着任何知识的工作——我干过管仓库的工作,干过法律文书的工作,干过推销员的工作;我在钢铁厂干体力活,又在剧院里打杂;正当我想着读书的时候,书真的来了,哲学的文学的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都是好书,堆成了山,又打成了捆,一捆码着一捆;我操作着一台废品站的压力机,把它们统统碾得粉碎……
“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怎样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

美丽的女子甩出粪水,精装的书籍化成纸浆的洪流。赫拉巴尔讲述轶事的方式,总是含有一种致人作呕的趣味,他直视并描绘腐臭和衰朽,把污秽和体面一道视为过程中天然的成分。在他大量流传于地下的故事中,思想、事物和情感会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而一手实现这种转化的人往往是他的英雄。《温柔的野蛮人》里,一个类似行为艺术家般的人物,在和女孩幽会的时候,突然把领带系在一棵苹果树的枝杈上,然后迅速绕到自己脖子上,把自己吊起来,还吐出舌头。让甜蜜与新生瞬间滑入恐怖与死亡,是恶作剧的旨趣所在。
在赫拉巴尔早期写的故事《施洗》中,一名喜欢打猎的神父,在驾车去施洗的路上,看到一头鹿正在过马路,他故意撞了上去,然后像猛兽一样,把尚温的鹿尸拖上汽车,用云杉树枝剖开它的尸体。
对肉身的持续执迷,定睛观看它的腐化和毁灭,就会抵达令人作呕的血腥秽臭。神父的职责,本来是用施洗来为受洗者的生命注入各种神性的意味,但他却告诉受洗孩子的父亲:“只有你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你不能让生命成为“另一个象征”。但这种对生命的肯定,在赫拉巴尔这里是与扼杀生命互为一体的,这个“生命”也可以替换为“事物”,或者“爱情”,或者其他种种实体。在《过于喧嚣的孤独》里,废纸打包工讲述他如何碾碎一捆捆、一包包书本时,总是让人分不清他到底是痛心还是狂喜;在《温柔的野蛮人》里,一枚婚戒被珍爱着它的人抛出了火车车窗。
我没有自我
赫拉巴尔是在父亲开的啤酒厂边上长大的,他后来住过的地方,也总是离不开酒气。从自传意味浓厚的小说来看,他活在特别鸡零狗碎的日常里,一会儿是水管子爆了,一会儿是墙皮掉了,一会儿火炉子灭了,一会儿邻居又在吵架骂街了——可是只要有酒力加持,他都能不为所动,云淡风轻。
直到近50岁开始职业写作之前,赫拉巴尔都在奋力地向现实下沉,如他本人所说:“现实中暗淡、粗糙的一面嗖嗖地向我袭来,像暴风雪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而我,没有梦想和反思,而是非常喜欢现实的样子。”在诸多他干过活的地方,钢铁厂尤其值得一说:那是距离布拉格40公里的克拉德诺,由奥地利资本家于1889年开办的波尔蒂钢铁厂,二战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命脉,赫拉巴尔在那里干了4年,拿着挣来的辛苦钱在布拉格安了家。4年后,他离开钢铁厂,又找了一份给剧院的舞台做布景的杂工。
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每一个工种都是为建设国家而服务。在布拉格,无论哪个公民都不允许拥有特权,人人都得自食其力,收入相差不大,住的也都是楼房,楼房里没有保洁员,没有洗衣服务,没有房屋修理工,没有配套的物业,一切都要自己动手。
当工人的赫拉巴尔自己运煤块,自己烧炉子,自己擦地板和洗衣服。他在《我是谁》《巴比代尔》等作品中,一再地刻画粗陋的生活环境,和他近乎求仁得仁的满足。我本来就没想要比别人过得更好——他说——我只想通过工作,通过和别人一样劳动、一样生活,去接近每一个人;我在这里拿着抹布擦地板,我擦了又擦,直到把我家门前的这块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的日子过得如诗一样;我安心地穿过飘着公共厕所消毒水气味的楼道,钻进自己的斗室,在那里铺上了干净的白桌布,生起了炉子,把鲜花插进玻璃瓶,打开从街对面打来的一罐啤酒,翻开书本。
赫拉巴尔说,他没有自我,总是不清楚自己最想去做什么,也经常做出一些让自己都失望的选择。然而无论处在怎样的情况,惊奇和专注,迅速聚焦于某个事物,是他从未放弃的天赋,也是他作家潜能的表现。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总是习惯于去叠那张账单,把账单的四个角一个一个地折起,然后再翻开。
来到剧院,他一向对看戏毫无兴趣,却在干了一阵子后,跟那些演员混在一起。他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跟他一样都是羞涩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很善良,而善良在当今已经不吃香,他们正是为此而羞涩。
在波尔蒂钢铁厂时,厂里竖立着一个硕大的厂徽,他每天去看,厂徽上,有一个卷发女人的美丽侧脸,在前额的地方还有一颗星星,他每天看那张脸,看它在烟囱喷出的一道道烟柱里面,是不是又黑了一点。1950年,36岁的赫拉巴尔写了一首诗,诗名叫“美丽的波尔蒂”。这并不是一首讽刺诗。他说:“你要是知道我有多爱波尔蒂钢铁厂,你会嫉妒我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切,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刻起,我就成了一个先知。那张脸,那颗星星,我在这里干了4年,那星星也为我加冕。”
赫拉巴尔也写那些“干一行爱一行”的普通人。他对铁路格外熟悉,1965年,他出版了《严密监视的列车》,被导演门泽尔改编为电影后,1968年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他的铁路知识源于一位舅舅约瑟。在《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此人变身为一个铁路信号员佩平,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路的交叉口,把升降杆抬起来,放下去,抬起来,放下去,火车在他眼前无数次地安全通过。这么一个单调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占去了这个人的40年生命。
当佩平终于退休时,他感到一旦离开信号塔,生活就毫无内容和意义。于是,他从一个边境火车站找到了一套二手的信号装置,把它搬到了自家花园里,又找来了一些铁轨和三节车皮,在树林之间铺设了一条循环的铁路线。然后,他就约了几个铁路上的老朋友一起,周末时一圈一圈地在花园里开车,他自己继续担任信号员的工作。周围的孩子都被他们吸引了过来,和他们一起乐而忘返,直到日薄西山,他们摇摇摆摆地结伴走向酒馆。
当职业终结时,热爱会成为什么样子?会像生命在腐烂时一样激发新的沉醉吗?
黑色幽默与浪漫
赫拉巴尔工作过的波尔蒂钢铁厂,后来逐渐衰败了。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老政权走向末路,昔日的工厂和工棚全都被废弃了,它们的窗玻璃全是碎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个躺倒在地、七窍流血的死人;机器都没人用了,被拆光了,稍微还值点钱的金属都被偷了个干净;通过厂区的铁轨锈迹斑斑,被杂草吞没;烟囱成了废墟里的一根根柱子,它们也死了,但它们的污染把工厂周围的土地折磨得奄奄一息,让地方政府不得不一年年投入重金,去整治环境。
对此,赫拉巴尔援引犹太人的圣书《塔木德》作了他的解释。《塔木德》里有一句经文,说人就像橄榄,只有在被压碎的时候才会吐出自身的精华;同样,捷克人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死了被烧掉后,所剩的东西才是宝贵的。基于此,令人恶心的衰朽和腐臭,在赫拉巴尔的笔下依然是衰朽和腐臭,却增加了一缕在生死之间游刃有余的快感。
在《过于喧嚣的孤独》里,主人公的妈妈去世了,他从殡仪馆里捧回了妈妈的骨灰盒,把它带给舅舅。他舅舅——那位铁路信号员——当时正在花园的信号塔里,沉浸在指挥火车的欢乐之中,当骨灰盒交到他手中时,他掂量了一下,随后又把骨灰拿去过秤,然后跟他外甥说:这里面装的不是你妈妈,你肯定拿错了,她活着的时候体重75公斤,正常情况下骨灰应该比这还多50克才对。不过,他们两个还是把盒子打开,把骨灰撒进甘蓝菜地里,因为妈妈生前最爱吃甘蓝菜,后来,被这骨灰滋养生长的菜,果然也非常好吃。
我们管这叫黑色幽默,但是赫拉巴尔真的让人嫉妒。生活对他开的每一个荒诞的玩笑,他都给出了更荒诞的回应。各种卑微,都能博得他的发自内心的欣赏,甚至连污秽他都可以回味。曼倩卡出了丑,羞愤地走了,他去寻找她,说我们还有事情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出丑的时光有待我们共度。
在另一篇小说《婚宴》中,赫拉巴尔正式地向读者介绍了他的妻子:
他这位妻子和曼倩卡一样,也是个乡下姑娘,也活在卑微的感觉之中,相信自己是被生活捉弄的对象。她在布拉格的巴黎饭店里做帮厨,环境和岗位,都不允许她有任何的个人野心,更不敢想象有人会爱上自己。但是,有一个晚上,她偶遇了正在楼道里擦地板的赫拉巴尔,她怯生生地跟他说话,生怕冒犯了这位据说忍辱负重的法学博士,可她很快发现,赫拉巴尔不仅没有任何的怨言,还要引导她去学习快乐。
当她再一次去那幢楼拜访的时候,她看见赫拉巴尔坐在二楼的阳光下,两个膝盖朝外面撇着,专心地在一架打字机上敲打着。他在写小说。他把打满字的纸抽出来,用一块小石头压在一沓纸里,再换上一张新纸,他说:我必须把这一点写完,才能下楼来看你,因为美丽的思想一旦敲门,我就得赶快请它进来。
在他的小说里,浪漫也得用这种家常唠嗑的方式来描绘。1963年,49岁的赫拉巴尔,在写了不少故事后,等到了政治气候松动、可以公开出版的机会。《严密监视的列车》《雪绒花的庆典》《温柔的野蛮人》,一本又一本地出来,他写得飞快,还亲手装订了《温柔的野蛮人》的头5本——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和谋生磨炼出了他的动手本领。1971年,他鼎鼎有名的《我曾待候过英国国王》,从构思到写完仅用了18天,也甚少修改。
但是,当他着手把他做废纸打包工的经验写成小说时,他感觉到这本书将是他最耗时日的工作。回忆,真实的体验,顺着他惯用的夸张的想象,一字一字地流到纸上:无数国家不需要,也不允许人民阅读的书籍,变成了废纸,它们跟花店的包装纸、废旧节目单、车票、冰棍纸、照相馆切割下来的照相纸尖角,还有办公室里扔掉的废纸、打字机色带、生日卡片、报纸、葬礼上用的纸花,以及屠宰场里血淋淋的包肉的纸……一起,被送到他面前,由他打包、切割、压紧、碾碎,最后化浆。
生活在朝这个人不怀好意地微笑:你不是喜欢劳动吗,你不是愿意跟所有人一样平凡地度过人生吗?你不是说,生命只有在死去之后,才能留下精华吗?所以,请你开动机器,去给所有这些废纸送葬吧。后来,他近乎是咬着牙一般写下这样的话:
“当我用20大气压的压力,把书本压成碎纸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人全身的骨头被碾碎的声音,我想到的是,那些书中真正的知识、精华终于被释放出来了。”
在荒诞世界的正中心
像那位铁路信号员一样,废纸打包的核心工作也是一个循环动作:在那台压力机前,他按下红色按钮,压板往前移动,按下绿色按钮,压板往后移动。这是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运动,无论你从哪里出发,最后都会回到原地。当你跃上巅峰,你就会跌落;当你沉入谷底,你又会浮起。在平淡之中发现离奇,捕捉让人哭笑不得的瞬间,这些,都是赫拉巴尔多年习得的看家本领,但是,当他在废品站干满了5年,将两只被化学药品伤害过的手再次放到打字机上的时候,他真正感觉到自己坐到了一个荒诞世界的正中心。
这个世界,谈不上什么人妖颠倒,一切都进行得那么的顺理成章;必然要衰朽的人们,送走那些先他们一步衰朽的事物,然后为一天的工作安然结束而干杯。这个以废品站打包工人为叙事主角的小说,就是《过于喧嚣的孤独》,他写出一稿,推翻,又写出一稿,又推翻,当他第三次重写并定稿之后,已是1970年代后期,他60多岁,而小说最后正式出版,还得再过14年。
很多西方人都受过《道德经》的震撼,赫拉巴尔在书中也写到过,他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理解,是老天不会优待也不会恶待任何人,老天有时候特别看重一个人,给他各种荣耀,各种春风得意,但一反手又遗弃他,让他丢光了脸面。但他常常讲起的,影响他一生的一句话,不是来自什么古代中西圣贤,而是在一家洗衣店里看到的“温馨提示”:有些污渍沾上之后是洗不掉的,只能把原物销毁。
这是赫拉巴尔亲身体会的真理:身上沾了大粪或煤渣、化学药品,或是被飞溅的钢花永久烫伤过的人,就必须带着污渍、臭味、坏死的皮肤和伤痕继续活下去,并且尽量保持笑的能力。他只在废品站干了5年,可是,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干了35年,在彻底无法摆脱书籍、废纸和地下室的世界之后,他被废品站开除了。
因为废品站引进了废纸处理流水线,新一代的打包工人,比他年轻,比他衣着体面,他们撕下一本本书的书皮、把书瓤扔进流水线的样子,更加灵活而老练,不像他那样,对书籍还那么的恋恋不舍。现在,他的笑,连同深深的八字形的嘴纹渐渐地凝固在脸上。在告别他的岗位时,他甚至没能像他舅舅带走一套铁路信号装置一样,带走一台他最依恋的机器。
《过于喧嚣的孤独》,正是那颗为赫拉巴尔的文学成就加冕的黑色星辰。当1997年2月3日,这位孤独多病的82岁老作家,费力地把书挪到床边,叠起来,然后探身而出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喂鸽子”。他坠楼了。在他衰朽死亡的美学行至终点时,这是一桩纯粹的、完美的自杀。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举报 文章作者
云也退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纪录片式书写中国村庄,魏思孝摘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纪录片式书写中国村庄,魏思孝摘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曾经在梁文道的《八分》中被介绍的作家山东作家魏思孝,在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凭作品《土广寸木》摘得首奖。
64 10-25 11:45 从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得主
从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得主在20世纪的100年里,女性获奖者只有区区9个人,起码有一半已经被遗忘。
351 10-18 10:50 约瑟夫·罗特:一个背井离乡、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
约瑟夫·罗特:一个背井离乡、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世界在解体,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一手笔走龙蛇,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
48 09-06 16:12 詹姆斯·鲍德温: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
詹姆斯·鲍德温: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鲍德温是美国的文化明星,在上世纪黑人文化的全明星阵容里,他占据一个无可争议的位置。
196 08-16 08:57 还原一个被焦虑、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
还原一个被焦虑、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谈论他成为一个符号什么是炒股杠杆,一个被消费的名字,一种能寄托许多情感的象征物,也是最常见的、很能显示作者阅历的缅怀卡夫卡的方式。
88 07-19 09:18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相关阅读
- 证券股票投资学 艾丽丝·门罗去世:她在世界一隅,慢慢挖出 129人看过
- 可靠的股票配资 欧阳修致仕与归隐后的生活:以酒为寄,聊志 60人看过



